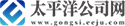
作者:张惠(广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严格说来,“短篇小说”这个文类并非古已有之,实际上它是在中国新文学发展之初,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过程中的典型产物,是在中国文学内部演进到一定阶段后,受到翻译的近代西方小说影响而逐渐成形的,并最终确立了“横截面”“经济(详略得当与精于结构)”“白话、不逾万字”的“短篇小说”范式。
周瘦鹃译《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书林书局影印版)
周瘦鹃创作的短篇小说《亡国奴家里的燕子》
开明书店出版的鲁迅小说集《一件小事》
1909年3月,由鲁迅和周作人翻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在日本东京出版。
1919年10月,胡适将自己1912至1919年间所译外国短篇小说10篇,结集为《短篇小说》第一集出版。
翻译:“它是采取进步而严肃的态度介绍欧洲文学最早的第一燕”
1909年3月和7月,由鲁迅、周作人兄弟翻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和第二册在日本东京出版,并在上海广昌隆绸庄寄售,此短篇小说集特别偏重北欧诸国作品。茅盾评价其译介优秀作家短篇小说的首创之功,“在他们计划翻译和出版的《域外小说集》中,俄国的契诃夫、波兰的显克微支、法国的莫泊桑、丹麦的安徒生,第一次以真朴的面目,与我国读者相见”;“这个短篇小说集是继续《摩罗诗力说》的主旨,介绍了俄国、北欧、波兰等国的反映人民痛苦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作品。这是第一次把反映被压迫的人民和被奴役的民族的叛逆和反抗的作品,介绍到中国。其用意和《摩罗诗力说》是相同的。”
由于《域外小说集》翻译主旨在于唤醒民众,所以更偏重于功能性而对艺术性的认识尚未称完备,翻译语言方面“句子生硬”“诘诎聱牙”;风格方面如蔡元培评价“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内容方面采用“直译”,对于当时国人还不能接受的某些宗教观念和道德问题,都没有曲笔掩饰,所以导致乏人问津的结果。冯至曾这样评价《域外小说集》:“我们不能不认为它是采取进步而严肃的态度介绍欧洲文学最早的第一燕,只可惜这只燕子来的时候太早了,那时的中国还是冰封雪冻的冬天。”
1917年,周瘦鹃将历年所译欧美十四国的名家短篇小说五十篇编成一部《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由中华书局出版。周瘦鹃选译的偏好和鲁迅相似。例如,鲁迅在1909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第二集里,曾“预告”下一期将推出“安兑尔然”(即安徒生)的作品,后来却没有出版。此后周作人只翻译了安徒生《第十四夜》的其中一节,1914年刘半农发表的《洋迷小楼》也只是对安徒生《皇帝的新装》的仿写,所以周瘦鹃翻译的《噫、祖母》才可以说是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安徒生作品完整的汉语翻译。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对鲁迅的主张隐有呼应之意。鲁迅曾经指出,中国才子佳人小说作家发现私定终身不容于天下,就用才子及第,奉旨成婚来解决,但是现实生活哪有这样称心如意,感情的威力也并非如此无远弗届。因此鲁迅认为,“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进而呼吁“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周瘦鹃用“翻译”来呼应鲁迅这一主张,《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选取了很多“惩情”之作,甚至还超前地选译了一组金钱侵蚀真爱的作品,如英国山格莱的《情奴》、英国哈葛德的《红楼翠幙》、法国伏尔泰的《欲》,都是女子为了金钱而放弃深爱她们的男子,或者搜刮直至对方破产。以至于翻译小说中发出这样的哀叹:“愿那天下的有情人,别做这种呆子……以后我愿普天下的男子,别识这一个不祥的情字,别做那情的奴隶。”这和中国元代王实甫《西厢记》的名言“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构成了绝妙的“反对”,这事实也代表了中国同西方、古典与现代价值观的激烈碰撞。
另一方面,周瘦鹃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对鲁迅的创作有催化之效。鲁迅在翻译《域外小说集》时就注意到安特莱夫的《红笑》并亲自翻译了几页,在周瘦鹃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中再睹《红笑》,在1918年4月便推出了与《红笑》颇为神似的《狂人日记》。虽然鲁迅在周瘦鹃的译文之前就通读过日译本,无须再待周译本的启发;周瘦鹃译本的叙述风格过于归化或雅化,不脱传奇文体的趣味,与《狂人日记》的深度写实风格不侔。但是从周瘦鹃译作中再睹《红笑》,当不免在鲁迅心中激起“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感受,故而可能对鲁迅的创作有“催化”之效。
故而,经过仔细的审视、思考和比较,当时身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科长的鲁迅,对周瘦鹃的译作给出如“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搜讨之勤,选择之善,信如原评所云。足为近年译事之光”的考语,并推荐和促使教育部在1917年9月24日给予“褒状”——“兹审核得中华书局出版周瘦鹃所译之《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三册,与奖励小说章程第三条相合,应给予乙种褒状,经本会呈奉教育部核准,特行发给以资鼓励。”
定义:“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
继周氏兄弟和周瘦鹃之后,1919年10月,胡适将自己1912至1919年间所译外国短篇小说10篇,结集为《短篇小说》第一集出版,收法国都德、莫泊桑,英国吉百龄,俄国泰来夏甫、契诃夫,瑞典史特林堡,意大利卡德奴勿等人的作品。1920年再版增入苏联高尔基小说一篇。胡适对鲁迅和周瘦鹃“珠玉在前”的译作念念不忘,他在《短篇小说》的《译者自序》里不无自负地谈道:“短篇小说汇刻的有周豫才、周启明弟兄译的《域外小说集》(一九〇九)两册,周瘦鹃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一九一七)三册。他们曾译过的,我这一册里都没有。”而胡适的译文集从1919到1940年再版21次,最终在影响力上一举超越了周氏兄弟和周瘦鹃的翻译。
综观胡适译《短篇小说》,有三点值得关注。其一,历经反复最终确定了用“白话文”作为翻译语言,用“直译”作为翻译理念。在翻译语言的选择上,1912年胡适的第一篇译文《割地》用白话文翻译;但其后1914年《柏林之围》和1915年《百愁门》都用文言文;1917年译《决斗》和《二渔夫》都用白话文;但同是1917年译《梅吕哀》则又是文言文,而且1917年还是胡适提倡“白话文”的一年。但自此之后,胡适的译文语言稳定为白话文。
是“直译”还是“意译”,胡适也曾反复游移。以标题为例,1912年《割地》(The Last Class)是意译;但其后1914年《柏林之围》、1915年《百愁门》和1917年《决斗》都用直译;然而1917年《二渔夫》(Two Friends)和《梅吕哀》(Minuet)则都是意译。1919年译的《一件美术品》和《爱情与面包》都为直译;可是同样是1919年译出的《一封未寄的信》(The Lost Letter),则又有意译的意味在内。因为原文说的是Lost,但是从正文总结,这封信不是丢失了,而是没有寄出,从而导致了男女主人公一系列的悲欢离合,所以胡适的译名其实更传神。1920年翻译高尔基的《他的情人》(Boless)则又是意译。这篇作品讲述一个名叫铁力沙的高大粗胖妇人,恳请“我”写一封信给自己的少年情人波尔士,“我”照办了。一两周后,铁力沙又来恳请“我”以“波尔士”的名义回信给自己。“我”几经周折才恍然大悟:“他在世上,没有朋友待他好,没有人用爱情待他,他只得自己心里造出一个朋友——一个情人来!”所以,高尔基的标题Boless本来指的是文中虚幻人物波尔士,但胡适参详其意,改成了《他的情人》。
其二,胡适在自己的翻译实践中领悟到“第一流”作家作品和白话的重要性。晚清梁启超等出于改良群治之目的,大力提高小说地位,并呼吁多翻译外国小说,使其中蕴含的科技、文化等进步因子通过小说这种通俗易懂的方式尽快实现移风易俗。疾呼引来响应,一时引发了当时小说翻译者占十之九、创作者占十之一的局面。然而弊端也很明显,翻译对象选择不管作家地位,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也被大量引进;作家的名字错译、改译甚至不译;作品内容意译、改译甚至自创羼入。胡适在翻译时,底本采用了美国纽约出版的《经典短篇小说(外国卷)》,该书是将法国、英国、俄国、瑞典、意大利等一流作家的经典作品萃为一集,而且每篇之前都附有作者小传,详细标明作者的姓名、生卒年和文学成就。胡适在翻译时不仅同样译出了作者小传,而且数年的矻矻翻译下,他对作家作品“本来面目”和“第一流”的重要性有了深入的认识。
翻译实践是促使胡适成为“新红学”开山的重要转捩,他1910年赴美,根据《藏晖室札记·小说丛话》所记,那时他对《红楼梦》的初步思考大致还是走“索隐派”之路,尤其不相信作者是曹雪芹。然而赴美之后,胡适一边从事翻译,一边进行对《红楼梦》的再思考,最终在红学研究方面不但选择了重视“作者”和“版本”的“考证”之路,且一转为主张作者是曹雪芹的“自叙说”,开创了红学研究的新典范。翻译实践也使他对当时国内翻译文学“鱼龙混杂”“文白俱译”的乱象提出了药方——1918年,胡适总结道:“现在中国所译的西洋文学书,大概都不得其法,所以收效甚小,我且拟几条翻译西洋文学名著的办法如下:一、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二、全用白话。”“第一流”和“白话”与胡适实现“创造本国新文学”的取法也是一致的。
其三,不同于鲁迅和周瘦鹃只实践,胡适还从理论上提炼和升华,提出“短篇小说”是西方一个专门的文类,且有特定的要求,不像当时国人以为仅以长短就可以划分。因此专作一文予以界定和概说,以高台宣讲促观念转变进而推动创作转型。
其实,在翻译《短篇小说》第一集出版之前,1918年3月15日,胡适先在北京大学演讲并将演讲词发表于《北京大学日刊》,后修订成《论短篇小说》,登载于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号,特别界定了“短篇小说”的概念和两个要点。胡适提出,中国文人不懂“短篇小说”,当时报纸杂志上的笔记杂纂,把篇幅不长的小说称为“短篇小说”是错误的,西方的“短篇小说”(Short Story)在文学上有特定的范围和要求。
他界定道:“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两个要点可简要概况为“横截面”和“最经济”。大部分继承史传传统的中国小说都讲求“纵剖面”式写作,即从头到尾叙述此人来历、此事经过;“横截面”则只取一段精华,以一点代表此人、此国或此社会,令读者窥斑可知一豹。“最经济”则要在有限的文字中精心布局结构,并能栩栩如生地写人状物。
胡适举自己所译法国作家都德两部作品为例,普法战争法国战败割地之后,被禁止再教法文,《最后一课》围绕一个小学生上最后一堂法文课展开,亡国惨状都由此小学生眼中见出。《柏林之围》写法国出兵进攻普鲁士,一位中风的法国老兵期待目睹凯旋,孙女只好天天假造法军得胜的新闻哄骗他,普兵攻陷巴黎进城时,听到军乐声的老兵误以为法军奏凯班师,竭尽全力穿戴整齐从窗口观礼却见到是普军,不堪打击倒地身亡。
胡适还在自己另一篇警醒国人鸦片之毒的译作《百愁门》中提及:“短篇小说大抵可分两种,一以布局胜,一以状物写生胜。吾前译诸篇,如法人都德之《最后一课》及《柏林之围》,皆以布局命意见长;此篇则状物之文也。”对于那些形式上是短篇,内容和手法却陈陈相因的传统写法,例如剿袭“某生,某处人,幼负异才……一日,游某园,遇一女郎,睨之,天人也……”套路的小说,胡适斥之为“烂调小说”,认为不能视之为“短篇小说”。
当然,除了胡适之外,其他理论家对“短篇小说”的界定也有思考和贡献,如1908年徐念慈已在《小说林》上发表《余之小说观》,提出了语言和字数的要求,主张“其文字,则用浅近之官话”和“全体不逾万字”。但是,真正从概念和要素揭橥“短篇小说”的要义,通过出版翻译的短篇小说集扩大影响,并事实上引发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短篇小说”创作潮流,应推胡适的首创之功。鲁迅、周瘦鹃、胡适三位文学大师及其所译的三部世界短篇小说集,既存在接续和争胜的关系,也存在提携和促进的关系,并通过接力,先引进、后界定,使“短篇小说”的概念和内涵不仅为国人所知所接受,而且由于和世界文学这个文类“同轨”而能够在同一赛道争驰。
实践: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短篇小说”示范之作
胡适对短篇小说的理论界定迎来了中国“短篇小说”的发展期,其中可以鲁迅、周瘦鹃和胡适本人的创作为例。
1919年7月20日在《每周评论》第31号,胡适发表了《一个问题》,小说选取的是“我”和旧同窗相逢之时,他仅大“我”一岁,时年三十,头发却早已花白,看来似乎比“我”大十几岁,对谈方知,旧同窗由于姻亲争家产、被裁员、多子女,以及妻病子殇等诸因素夹击,每天只为了糊口忙到深更半夜,没有任何休息和社交,最后发出人生到底有何意义的疑问——“人生在世,究竟是为什么的?小山,你是学哲学的人。像我这样养老婆,喂小孩子,就算做了一世的人吗?”这篇小说以“横截面”的写法,用一个男子半生奋斗却困顿无望这个点,反映了社会变迁和哲学之问的大问题,也践行了胡适所说以部分代全体的“经济”笔墨。
鲁迅的《一件小事》文末署“写于1920年7月”,实际上发表于1919年12月1日《晨报》“周年纪念增刊”上。该文叙述“我”入城年久,愈来愈看不起人,一天雇一个人力车夫出行,车把带倒了一个老妇人,“我”认为老妇人无恙,且路上无人看见,于是催促车夫不顾而去。车夫反而搀起老妇人询问她伤势如何,并把她送到警署去做检查。“我”陡觉车夫高大,而自惭渺小,这一件小事,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这篇小说用的是“扶不扶老妇”的“横截面”的写法,对同一件事两种态度反映了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和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也是以部分代全体的“经济”笔墨。
周瘦鹃《亡国奴家里的燕子》发表于1923年5月16日《半月》第2卷第17期,这更是一篇深受胡适影响的作品。其一,周瘦鹃与胡适讨论过直译和意译的翻译方法,并在后者的鼓励下在1936年由大东书局出版4册《世界名家短篇小说全集》。其二,周瘦鹃对胡适的作品颇为关注和熟悉,1928年他和胡适相遇时,“谈及二十年前之《竞业旬报》中有博士诗文杂作,署名铁儿,已斐然可诵”。其三,周瘦鹃《亡国奴家里的燕子》不仅是对《最后一课》的致敬之作,也较为完美地体现了胡适对“短篇小说”的界定。都德的《割地》(出于对近代中国不断割地赔款的忧愤,胡适最初没有直译书名而是根据小说内容意译为《割地》)是胡适的首译,也是他影响最大的译作,《闲话胡适》中提道,“尤其是《最后一课》对国人的影响最大。我回忆我阅读这篇爱国主义小说时,心情非常激动。后来,中小学语文课本中,都收入此文。我询问六七十岁以上老友,他们都读过这篇文章,也都有同感。”《最后一课》借一小学生之眼之口道出亡国之惨,《亡国奴家里的燕子》则借一燕子之眼之口道出亡国之惨。叙事者“我”原本是一只在主人家梁上过了十年安稳日子的燕子,第二年春分飞回旧巢,惊见小少爷已被刺刀捅死,小姐“倒在一个矮人的臂间”,竟被四五个矮人强暴,“我”的主人冲去救女,被这些外国兵用枪射杀,甚至燕子的妻子也遭流弹殒命。国破家亡,燕子伤心飞走,再次归来发现门上已改挂太阳旗。尤其最后“听得麻雀们唧唧叫着,似乎也变了声口,改说外国话了”,显系脱胎换骨于《最后一课》中那一段,“学校的屋顶上有一群鸽子在咕咕地低声鸣叫,我一面听着一面心里自问:‘那些人是不是也要强迫鸽子用德国话鸣唱?’”
启示: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吸收外国文学经验
胡适对“短篇小说”的界定和影响虽然兹体甚大,却同时会引来一个疑窦:中国传统文学历史悠久,难道就没有“短篇小说”而要迟至新文学时期吗?这也恰恰关系到中国古典小说到现代短篇小说转型的中国文学结构内部变迁问题。
追溯中国古典小说,其中含有“短篇小说”的因子却不能称之为现代意义上的“短篇小说”。在先秦时期诸子寓言,汉、魏晋南北朝、唐时期的叙事诗中也有“横截面”写法的因子。如《孟子·齐人有一妻一妾》讲述妻子尾随齐人,见到平日夸耀与富贵者饮宴的齐人,实际上只是到坟地里乞讨残羹冷炙,妻子回家与妾羞耻哭骂而齐人恬不知耻。如《十五从军征》仅选取八十岁老兵归家见到亲人死亡罄尽坟冢累累的场面,即道尽战争对人的戕害。如杜甫《石壕吏》选取天宝之乱时,作者投宿见到差役征兵,老翁逾墙逃走,老妇被捉的一夜之间见闻。又如白居易《井底引银瓶》选取私奔女子与父母断绝联系,来到夫家多年却不被公婆接纳,天地茫茫无处可去的绝境。
中国古典小说中也有详略得当和精于结构的“最经济”写法因子。详略得当如《木兰辞》略写战争,仅用“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一语带过,而详写木兰从军之难与归来之喜。“精于结构”如唐传奇《虬髯客》,虬髯客不仅见证李靖与红拂女的一段情史,而且有逐鹿中原之意,但忽然历史人物“太原公子裼裘而来”,于是虬髯客避其锋芒到海外创国,依然是唐太宗得了天下。虬髯客只是一个虚构人物,写来却好像真有其人其事;最终结果出人意料又毫不违背历史真实;虬髯客、李靖、红拂女各自形象活灵活现,这三重长处都可见结构布局的匠心。
然而,中国小说中有许多形同“短篇”,但或类似杂记随感,或类似流水账簿,例如宋代《宣和遗事》上段不接下段,没有结构布局,故不能视之为“短篇小说”。明清时期“短篇”有白话的“三言二拍”和文言的《聊斋志异》等,那么是否有可能水到渠成地自发形成“短篇小说”呢?在我看来,答案是否定的。一则明代之后,短篇的白话小说簇拢起来成为长篇白话章回小说,像《儒林外史》就是“形同长篇,实为短制”,反而阻碍了白话短篇小说的发展。二则短篇的文言小说由于语言的关系不能成为写人情世故的利器。所以,中国已有的小说“短篇”是一株生机盎然的母本,但要发展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短篇小说”硕果,需要外来因素的催化,即西方翻译小说的嫁接。
中国短篇小说的内部演进,从先秦寓言到魏晋《世说新语》《桃花源记》,再到汉唐一些叙事诗、唐传奇,明代白话拟话本小说“三言二拍”、清代文言小说《聊斋志异》等,还只是不断累积短篇小说的元素,却与现代意义上的短篇小说尚有本质上的区别。真正意义上的“蝶变”,一是来自一代文人的接力翻译,即鲁迅《域外小说集》、周瘦鹃《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胡适《短篇小说》,将世界名家短篇小说引入中国。二是来自胡适的理论定义,以一篇《论短篇小说》为其定性。三是胡适、鲁迅、周瘦鹃又分别亲自创作短篇小说《一个问题》《一件小事》和《亡国奴家里的燕子》垂范,最终确立了“横截面”“经济(详略得当与精于结构)”“白话、不逾万字”的“短篇小说”范式。
回顾“短篇小说”的定型,有三点特别值得关注之处:一、可以植物学的扦枝为喻,中国已有小说为母本砧木,外来翻译短篇小说为嫁接之枝条,最终融合生长为中国本土之“短篇小说”。二、是一个先实践后理论再实践的过程,而且历时十余年即告竣,充分体现了近代文学转型时期的迅捷。理论来源于翻译小说之实践,而且翻译与创作并行,是中外文学交流互动之成果。三、理论、翻译与创作之示范由三位大家鲁迅、周瘦鹃、胡适担纲,接力催生了“短篇小说”这一新文类,展现了一代文人探索现代短篇小说的理论与实践的艰辛过程。
在新文学承前启后除旧布新的节点上,一代文人之所以积极推进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力倡“短篇小说”,还因为有对时代和世界的把握,观察到当时世界文学的趋势都是由长趋短,由繁多趋简要。这种趋向的原因,一在于世界生活的竞争加速,时间愈趋宝贵,故而文学也愈趋短而精;二在于文学自身的进步,要能纳须弥于芥子,用简短的内容容纳丰富的内容。于是,他们通过翻译世界短篇小说来作为参考的样本,通过明晰的定义来界定“什么是短篇小说”,又用本民族的内容和白话文亲自创作本土的“短篇小说”,从理论和实践上推动了中国文学结构的内部变迁。
中华文明常以开放包容的心态面对外来文化并吸纳开新,南朝时佛经的翻译引起了对声律的重视,并将之引入到诗歌创作中,提出一套音韵平仄协调的规则,“四声八病”成为永明体的重要内容,并对唐代近体诗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近代“短篇小说”的发生发展又是一则显例,正是海纳百川的气度,实现了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有容乃大”、日新又新。
《光明日报》(2023年08月11日 13版)